十五从军征改写故事(一)
清人范大士在《历代诗发》中说:“后代离乱诗,但能祖述而已,未有能过此者。”
军中。中军帐外。80岁的老兵喜笑颜开——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白发苍苍的老兵突然间容光焕发,好象不是80岁,他的眼中又浮现出自己当年15岁小新兵的模样,想起了临行前夜,母亲依依不舍,油灯下一针一线仔细为他缝制新衣;出门时,父亲默默无语,倚门而立的身影又一次从他眼前闪过,弟妹稚嫩的叮咛又一次在耳边响起。
归途中。脚步匆匆,看不到败落的村庄,看不到流离失所的百姓。飘零的风雨再也阻挡不了他前行的脚步。脚步匆匆。
家乡。他终于回来了,在离家65年之后回来了。村口的大杨树挺立依旧,村中的房子却变矮了,破败了。他犹豫了。满目凄凉,满目生疏,家在何方?
“你们谁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呀?”“告诉我,我的家在何方?”无数次询问,无数次茫然,竟没有人认识他了么?终于找到了一位年过古稀的老者,“你是——”他欣喜若狂,一把抓住老者的手臂,“是我!是我!我家里还有谁?”唏嘘良久,老者伸手一指,目光到处满是松柏掩映下的高高的坟茔。他蓦然呆了。松柏?荒冢?这和他有什么关系?难道——跌跌撞撞,踉踉跄跄,许久许久,才来到了旧日的家门前。家,是他的家吗?他推开了仿佛记忆中模样的歪斜的大门,吱——尘土飞扬,惊走了正在院中玩耍的野兔,坍塌的院墙下自有兔子出入的门户;小心的拨开茂盛如林的旅谷,步履艰难的他终于来到屋门前,倚门而立的父亲如今已不见了踪影,他要到哪里去寻觅亲颜?身在家中的他犹如置身孤寂的荒漠,幼小弟妹的声声呼唤犹在耳畔回响,亲人的面孔却再难相见。一只雉鸡仓皇间从梁上飞出,扰乱了他的思绪。这是我的家呀?这是我的家吗?仰望苍天,苍天无语;俯问大地,大地无声。一路的欣喜,一路的渴望,都已化为了泡影,眼前景物依旧,旧日的亲人却不知所终。
环顾四周,景物无言。疲惫的他拖着同样疲惫的身子撵飞了霸占屋梁的雉鸡,轰走了占据庭院的野兔,找到了记忆中的水井,一点点舂净了旅谷的外壳,点燃了灶内的烟火,缕缕炊烟袅袅升腾,缕缕饭香扑入口鼻。一只只洗净了的旅葵叶子从他的手里滑入锅中,片刻后,清新的旅葵香气在屋内升腾。
望望煮熟的饭菜,望望空空的庭院,呆呆的他不知道和谁来分享。信步来到门前,遥望松柏掩映下的坟茔,泪水无声的滑落,打湿了满是尘土却再无人补缝的衣裳。
十五从军征改写故事(二)
“狗子,你千万要小心!一定要活着回来!”一位满头白发的母亲深情的对儿子说。此时,太阳照耀着大地,小路两旁柳枝摇曳,沙沙作响,展现着春的气息,一名正值十五六岁的少年,背着包袱,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喜悦。旁边是他的母亲正在嘱咐少年。而那名少年正是我。今天是我从军出征的日子。
因为战争的频繁爆发,朝廷大量招兵买马,我就是其中一名小兵。没想到的是,这一别却使得我悔恨终生!
……
转眼,几十年过去了,村边的柳树早已不复存在,一个狼狈不堪的老人正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步艰难的走着,这个老头就是我——狗子。
六十五年了,整整六十五年了!这战一年一年的打,我也年年都不能回家。在每一场战役中,我都可大可小的受了伤,也经历了许多。睡死人堆,啃草根,吃腐肉,什么我都过了,每每这时我都想着回家!是“家”这个字在支撑着我,不然我恐怕早已化为一掬黄土了吧!对面走来了一个人,哦!原来是我村里的王麻子啊。他面色枯槁,形如纸灰,皮肤暗黄透青,像一个饿死鬼一样。我拄着木棍走向前问:“王麻子,你怎么成这样了?发生了什么事?我的家人还好吗?”我一连珠炮似的问他。他楞了一下,然后说:“要打仗,官爷强收了俺们的粮食,还加重税,俺们村里的乡亲们饿死的死,逃走的逃走,只剩下俺们几个没地去儿的。”说到这里他欲言又止,“呃…你的爹娘他们……呃,唉!你自己去看吧。”我心中的不安隐隐扩大,我匆忙与王麻子告别,踉跄的跑回了家。
我呆呆地站着,两眼无神,全身颤抖着,“不!这不是我的家!爹!娘!哥哥!狗子回来了!你们在哪?”我发疯似的冲进院子,身上的骨头都在向我控诉,可我顾不了这么许多了!
院中有三个黄不拉几的土包,微微的凸起,旁边是两棵松树,野兔肆意的穿入狗洞,野鸡在房梁上乱扑腾。房屋两旁是野生是谷子和葵菜,杂草丛生,仿佛向我炫耀着:这是他们的天地!我深深地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泪水被我强忍在眼眶里。我不断抖动着,缓缓地跪下,向那三个土包磕了三个响头。一个,额头红了,两个,血丝现了出来,三个,血流了。我不想管额头上的伤,只想好好地叩三个头。这是对父亲,母亲,哥哥的悔,是对战争无情的恨!!!
磕完了头,我静静地收拾了庭院,吃完了饭。沉默地走到了门口,看那太阳将要落下,急哦像是人的生命一样,走到了尽头。不禁回忆起与父母,兄长在一起的日子,那快乐的时光。一直强忍着的泪终于在这时忍不住了,他们争先恐后的涌出眼眶,顺着脸庞流下,沾湿了我的衣服。好累呀,疲倦了,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小池塘边,看那太阳即将落下,仅剩下最后一缕光辉,呵呵,我的心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像这塘水般平静。我笑了笑,阖上了眼,光同时也消失了。黑暗笼罩大地…
咚——一个重物落入水中,一声闷响,水面漾起圈圈涟漪后,又重归平静……
十五从军征改写故事(三)
我是一个老兵,当年为了驱逐匈奴。我被迫告别父母,瞒着怀孕的妻子,卖掉了赖以耕地的黄牛买了兵器鞍马,就这样随军出征了。几十年的刀光剑影、金戈铁马,我看过无数的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,我像一具行尸走肉冲冲杀杀,在边关我一呆就是几十年。
现在,我老了,牵着一匹瘦弱的马,赶着回乡还是很高兴。心想:父母还在吧,妻子儿子都怎样了,孙子该有了吧。我想着回家,想着五亩良田,想着天伦之乐,我归心似箭。在前线多少个日日夜夜想念着的父母妻儿,我就要见到他们了。
走近家乡,家乡的山秃了许多,在秋天,落叶像黄蝴蝶一样飘着,翻过山头就可进村了但是村里变了,变得让我感到陌生。村里萧索破败毫无生气,几处颓垣断壁杂草丛生,这时一个面容枯蒿的男子牵着一头老牛从我面前走过,我兴奋地上前询问。多少年来不管我的头发掉了多少,白了多少,我的乡音依旧未改。男子听了出来,“哦,你是锁二叔,你家。在那山脚边。”我很激动:“哪儿!”“那儿有几棵松柏树的地方。”男子回答。我激动兴奋踉跄地奔过去,几十年的等待,今天要实现了,我几乎落下泪来。
哦,对就是那儿。陌生而又熟悉,在梦里魂牵梦绕了千万次,几十年前那个秋天月夜,我就是从这走出去的。泪水模糊了我的双手,我好像在做梦,我又在想象在家中的情景,父母妻儿、儿媳妇……我推开门,扑了进去。我有点害怕,很失望,我被眼前破败的景象吓呆了。野兔从狗洞进进出出,野鸡在残垣断壁间飞来飞去,院子里长满了和人一样高的杂草,井口残破不堪,布满青苔。()我好像被人用棒子打破了头,昏昏沉沉,耳朵里嗡嗡地响。三座坟墓啊,我眼前直发黑,我的腿一点不听使唤,直发软,很重很重。乡里人告诉我一座是父亲的、一座是母亲的,一座是儿子的,我喊不出声,只是口中“啊……啊……!”内心疼痛万分。
原来,我走的第二年父亲死了,第三年母亲死了,第五年,儿子死了,妻子昵?乡里人说家都没有了,妻子还能呆下去吗?
我拖着一具空壳,走进家中,眼前又浮现出几十年前的景象,父母妻儿的音容笑貌就像在我眼前忽然出现。我坐在厨房的凳上,稍微休息一下,然后在院子里扯一把野草野菜,找一个破锅生火做了一点汤饭,但我一点都吃不下,我一瘸一拐地出去,门前的青石板没变,树荫没变,小溪没变,物是人非,我端着饭菜望着天边的夕阳落下,金黄的夕阳映在墙上,黑夜的黑暗即将吞噬一切。我瘫坐在井口,是在沉思,又好像在回忆。我不知道饭菜能和谁分享。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浸湿我破旧的衣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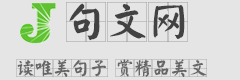
 鄂公网安备42010502001473号
鄂公网安备42010502001473号